案例概要
仲裁协议与担保合同。申请人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条款无效,法院认为其一,根据《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第97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在主合同和从合同中分别约定诉讼和仲裁两种不同的争议解决方式,应当分别按照主从合同的约定确定争议解决方式”。本案中,主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是诉讼,而从合同《保证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是仲裁,应当分别按照主从合同的约定确定争议解决方式。黄晓旋主张按照主合同的约定确定《保证合同》的争议解决方式,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二,案涉《保证合同》第十四条第二款约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无效的情形,亦不属于该法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的需特别提醒对方注意的免除或者减轻格式条款提供方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黄晓旋以仲裁条款是格式条款为由主张该条款无效,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法院裁定驳回申请人的申请。
案例情况
审理法院: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23)粤01民特1460号
裁判日期:2023.09.13
发布日期:2023.10.13
申请人:黄晓旋
被申请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证券公司)
案件背景
申请人黄晓旋向本院提出申请:1.请求确认(2023)穗仲案字第6515号案中山证券公司提交的《保证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无效;2.本案申请费用由中山证券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案涉《保证合同》系从合同,其争议解决方式应从属于主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案涉《保证合同》系从合同,从属于主合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主合同争议解决方式为诉讼,中山证券公司针对主合同向法院提起诉讼,针对从合同向仲裁庭申请仲裁,既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利于案件审理。此外,主合同与从合同从整体上看,本质上系一个合同。主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为诉讼,从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视为对整个合同的争议解决方式没有约定,即案涉合同并不存在有效的仲裁条款。
二、案涉仲裁条款因系格式条款而无效。虽然中山证券公司向仲裁庭所提交的《保证合同》第十四条约定了法律适用、争议解决方式,但该合同系中山证券公司单方面印制的格式合同,其限制了黄晓旋重要的诉权,加重了黄晓旋维权的难度。此外,该条款亦没有采取增大字体、加粗等方式进行明示、强调,与普通条款无异,黄晓旋难以发现该类无效条款。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和第四百九十七条的规定,案涉《保证合同》的格式条款属于无效条款,本案不存在有效的仲裁条款。
三、案涉仲裁条款因约定不明而无效。即使认为《保证合同》第十四条不因上述情况而无效,但该条第二款内容应认定为约定不明:(1)双方关于仲裁事项,没有明确约定。该条款约定“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并不是一个明确的争议事项,是一个笼统的表述,属于仲裁条款对仲裁事项约定不明确,双方也并未签订补充协议补充,该仲裁条款无效。(2)该条款中仅载明“协商不成的,提请广州仲裁委员会东莞分会(仲裁地点在东莞)”,但并未明确提请广州仲裁委员会东莞分会进行何种处理,因此该条款应认定为约定不明而无效。
四、本案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案涉《保证合同》第十四条明确了发生争议应该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才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因此,协商解决是本案当中的仲裁前置程序,即使认为仲裁条款有效,但其提交仲裁之前也必须履行这一前置程序。但本案中,中山证券公司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该前置程序,因此不能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综上,为维护黄晓旋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裁决,判如所请。
被申请人中山证券公司辩称,黄晓旋提出的申请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全部请求:
一、案涉《保证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合法有效。该合同第十四条仲裁条款有明确的仲裁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和仲裁委员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仲裁协议合法有效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且不存在该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仲裁协议无效之情形,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此外,合同争议的解决是一个独立关系,主从合同是实体问题,仲裁条款是程序问题且为独立条款,故应按照独立关系来确定管辖权的问题。
二、黄晓旋主张本案争议解决方式应从属于主合同及案涉仲裁条款无效的理由不成立。1.案涉《保证合同》约定了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人民法院对本案纠纷无管辖权。虽本案主合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诉讼,但因本案担保合同《保证合同》约定了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以及《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因案涉《保证合同》所产生的纠纷不享有管辖权。
2.案涉《保证合同》中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不属于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选择“提请广州仲裁委员会东莞分会”作为争议解决方式,并没有不合理地免除或减轻中山证券公司的责任或加重黄晓旋的责任、限制黄晓旋主要权利的情形,因此该仲裁条款约定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所规定的无效情形。
3.案涉仲裁条款约定明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仲裁协议合法有效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案涉《保证合同》有中山证券公司的盖章与黄晓旋签字捺印,证明双方对于其中约定的仲裁条款也已进行确认,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保证合同》第十四条已明确仲裁事项为双方因履行案涉《保证合同》所引起的争议;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为广州仲裁委员会东莞分会。
4.本案中双方约定“首先应协商解决”是形式,“协商不成”是结果,中山证券公司申请仲裁的行为应视为已出现“协商不成”的结果,广州仲裁委员会东莞分会有权受理本案。
经审查查明:
2017年7月6日,马鸿(甲方,融入方)与中山证券公司(乙方,融出方)签订合同编号为20170008的《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约定有关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双方的相关权利与义务、提前回购与延期回购、履约保障措施、权益处理等内容,该协议第十五章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约定了争议解决方式为诉讼。
2017年7月10日,马鸿与中山证券公司揭阳普宁河滨路证券营业部签订交易编号为20170008-1的《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约定了双方交易类型为初始交易,标的证券代码为002503,证券数量为42500000股,标的证券价格为7.06元/股,初始交易日为2017年7月13日,回购期限为728日,初始交易金额为1500000000元,预计回购金额为167290000元,购回交易日期为2019年7月11日等内容。
2020年12月14日,黄晓旋作为甲方保证人与乙方债权人中山证券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ZSZQ-DGYH-SYT-3]的《保证合同》的从合同,该保证合同约定“为担保本合同第一条所述‘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甲方愿意向乙方提供保证。双方经平等协商订立本合同。出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合同中的词语解释依据合同确定。”案涉《保证合同》第一条约定主合同为中山证券公司和马鸿(债务人)于2017年7月6日签署的协议编号为[20170008]的《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2017年7月10日签署的编号为[20170008-1]及其修订或补充协议等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存续期间马鸿签署的《中山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交易协议书》(补充交易)、2019年7月10日签署的编号为[20170008-2]的《中山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交易协议书》(延期交易)、2020年7月7日签署的编号为[20170008-3]的《中山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交易协议书》(延期交易)、2020年12月14日签署的编号为[20170008-4]的《中山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交易协议书》(延期交易)。第二条约定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如有多个保证人,各保证人为连带共同保证人,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第十四条第二款约定了在保证合同履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首先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请广州仲裁委员会东莞分会(仲裁地点在东莞)的争议解决方式。《保证合同》尾处甲方处有黄晓旋的签名和捺印,甲方配偶处有马鸿的签名和捺印,乙方处有中山证券公司的印章及其法定代表人吴小静的个人印章。
2023年4月7日,中山证券公司根据上述《保证合同》第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仲裁条款,以黄晓旋为被申请人,向广州仲裁委员会东莞分会提起关于保证合同纠纷的仲裁申请,案号为(2023)穗仲案字第6515号。黄晓旋在该仲裁案件开庭前向本院申请确认上述《保证合同》第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
法院认定
本案为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纠纷,故本院仅对案涉仲裁协议的效力问题进行审查。
其一,根据《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第97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在主合同和从合同中分别约定诉讼和仲裁两种不同的争议解决方式,应当分别按照主从合同的约定确定争议解决方式”。本案中,主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是诉讼,而从合同《保证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是仲裁,应当分别按照主从合同的约定确定争议解决方式。黄晓旋主张按照主合同的约定确定《保证合同》的争议解决方式,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其二,案涉《保证合同》第十四条第二款约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无效的情形,亦不属于该法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的需特别提醒对方注意的免除或者减轻格式条款提供方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黄晓旋以仲裁条款是格式条款为由主张该条款无效,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案涉《保证合同》第十四条第二款约定明确仲裁事项为双方因履行《保证合同》所引起的争议,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为广州仲裁委员会东莞分会,有明确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和选定的仲裁机构,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也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所规定的无效情形,依法应认定为有效条款。黄晓旋主张案涉仲裁条款因约定不明而无效,与事实不符,于法律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其四,黄晓旋主张协商解决是仲裁前置程序,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申请人黄晓旋申请确认仲裁条款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黄晓旋的申请。
案例评析
仲裁协议与担保合同。主合同与担保合同,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有疑问的是,主合同关于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能否约束从合同?在(2017)京04民特32号民事裁定书中,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指出“……对于该担保的争议解决方式,担保函中并未进行约定,同时相关法律亦无主合同约定仲裁条款,担保合同亦应适用仲裁的规定。因而在EEI公司与万源公司未就担保的争议解决方式达成仲裁合意的情况下,贸仲认为《采购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应同样适用于该担保函的管辖处理意见,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担保部分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一条曾规定,“债权人一并起诉债务人和担保人,主债权债务合同和担保合同均约定了争议解决方式或者管辖法院,约定不一致的,应当根据主债权债务合同的约定确定主管或者管辖事项;未约定争议解决方式或者管辖法院或者仅担保合同作出约定的,根据主债权债务关系确定管辖法院”。不过,正式稿对此进行了实质性调整,第二十一条规定“主合同或者担保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的,人民法院对约定仲裁条款的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无管辖权”。本案例中,法院指出“主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是诉讼,而从合同《保证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是仲裁,应当分别按照主从合同的约定确定争议解决方式”。这一认定,值得赞同。
本案例涉及的另外一个问题,格式合同情形下,提供方是否需要对争议解决条款进行特别提示?法院认为,“……不属于该法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的需特别提醒对方注意的免除或者减轻格式条款提供方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从实践情况来看,这一观点相对少数。如在(2023)京04民特445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涉合同条款具有事先拟好、反复使用以及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合同相对方协商的特点。其中的争议解决条款是合同的主要条款,应属于与当事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作为该协议制定方,粉笔头教育应向合同相对人胡方斌履行提示或者说明的义务”。又如在(2023)京04民特256号民事裁定书中,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争议解决条款是合同的主要条款,应属于与当事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作为该协议制定方,中安教育应向合同相对人牛亚平履行提示或者说明的义务”。不过,一般认为,约定仲裁不属于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如在(2023)沪74民特5号民事裁定书中,上海金融法院指出“诉讼与仲裁作为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各有优劣。与诉讼方式相比,仲裁解决纠纷具有高效快捷,一裁终局的特点,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对合同各方主体均是平等的,不能认为是对一方当事人主要权利的排除,亦不存在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的情形”。
作者:张振安律师(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文章来源:临时仲裁ADA

 中国政府网
中国政府网 无障碍版
无障碍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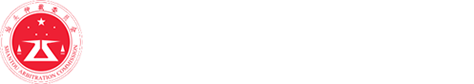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 :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 : 
 粤公网安备 44051102000227号
粤公网安备 44051102000227号